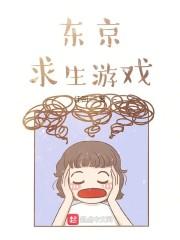多肉小说网>谋杀那个心理医生 > 第25章(第1页)
第25章(第1页)
缺氧的感觉让她几乎濒临死亡,甚至比死亡还要恐怖,心跳声在耳边轰鸣,让她怎么都觉得不自然。
如同火烧般灼热着祝余的身体,她就要失去了心智,就在刚刚,在牧之用着那种眼神在看自己的时候。
她一把掀开被子,扯下吊针后顺着牧之的方向走去。
“牧之。”
前者转头拂去额上的刘海,脸上还带着似是勾人的妩媚笑容,“你现在就想出院吗。”
祝余咬了下后槽牙,又顶了下脸颊上的软肉,随后从口袋里取出眼镜用手指硬生生掰碎。
她用尽全力,在病房门口跑向站在走廊尽头的牧之。
手指上沾染着鲜血,就差一点就要割破牧之的喉咙,但她没这么做,对方那双求生的眼神让她停下了手上的所有动作。
牧之捂着喉咙的伤跑着离开了这里,祝余望着满手的红色液体不知所措,皱着眉头想了很久。
等到回过神,或者说是被医生采取强制措施,打了麻药又重新穿上束缚衣,坐在小黑屋里。
祝余直勾勾盯着眼前的长发女人,昏暗的灯光下让她认不清这人是谁,恍惚中她把这人当成了阿也。
清纯无邪的眼里落下一滴泪,接着是哽咽的声音,她能见到站在暗处的人是自己的父亲。
“眼镜从哪儿来的,老实交代。”
祝合严厉的话在这间不大的小黑屋里想起来,让祝余只觉得背后一阵发凉。
祝余支支吾吾地回答道:“阿也的遗物。”
“周浅近视吗。”
他叉着腰反问起脖子上缠了一圈绷带的牧之。
“近视,但没配,至少是在我和她彻底没了联系之前她不戴眼镜,我看那副眼镜的款式不像是她喜欢的,反倒是……”
话已至此,牧之走向祝余,双手撑在面前的桌上,眼睛直勾勾盯着对方,“你会留在身边的东西,我记得你近视对吧,而且还不低。”
被直面的拆穿谎言的祝余避开了这番攻势,接着她的沉默让整个屋子如死了一般寂静。
藏在衣服中的指甲陷进皮肤里,面上仍旧坚持刚刚的那番说辞。
“这副眼镜就是阿也的。”
牧之蹙眉面露难色,“我可不知道阿也戴眼镜。”
“你不是她,又怎么能知道,况且只是一副眼镜,她似乎没这个必要与你这个前任报备。”
前任这两个字被祝余落下重音,她反复强调牧之所扮演的就是一个初恋的角色。
眼看问不出什么,牧之只好重新回到一开始的位置,手肘故意撑在祝合的肩膀上,摆出头疼的模样。
嘴里还嚷嚷着什么,头好痛,要炸开了,这些话;一瞬间让所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她,其中包括祝余。
审讯位上的某人故意笑了一声,“演技还是这么差,难怪你留不住阿也。”
祝余的嘴还是这么毒。
牧之瞥了一眼过去,接着继续捂着太阳穴,“哎呀呀,好疼,好疼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