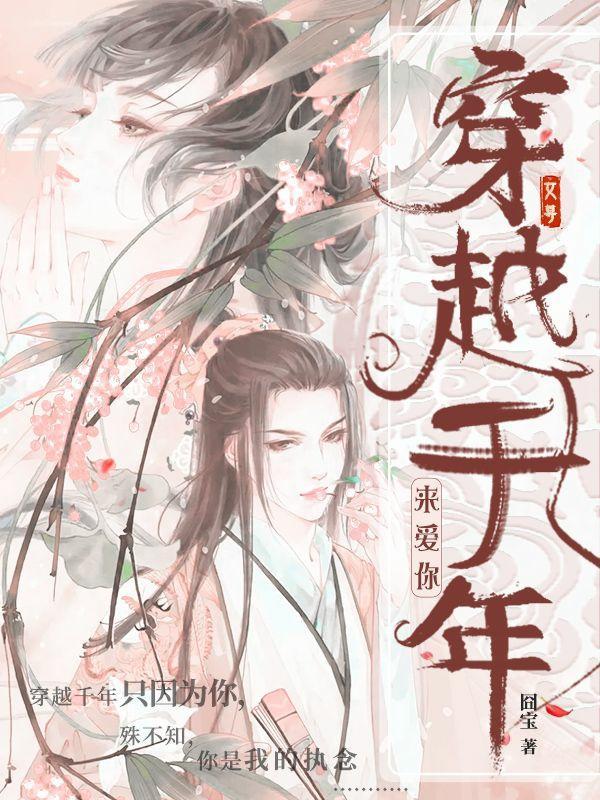多肉小说网>在末日中漫步,直到世界尽头 > 第201章 伏羲智能与钱明的释怀(第3页)
第201章 伏羲智能与钱明的释怀(第3页)
路雪狼吞虎咽地吃着桌上的菜,米饭盛了一碗又一碗,白沙将自己的狗盘舔得干干净净,正一脸期盼地看着我。
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楚月的话。
她说得话我大概能够理解。
可我好像并不能帮上什么忙。
于是这场晚宴在不愉快中分崩离析。
最先走的是楚月,她说自己吃饱了,再然后是周天乐,她临时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
留下来的是钱明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,他对我说道:
“以前的事我想开了。”
“这我知道。”
我回答。
否则他怎么会开口帮吴不知说话?
“任何一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,就像一个患了绝症,病得要死的人一样,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,甚至还会有上瘾的不良作用,那你会不会选择注射呢?”
“你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,是一种犯罪,可你给一个垂危的病人注入吗啡,却有可能是重生的希望。”
“非常时期有非常的策略。”
“道德不是空泛的,不是孤立存在的,那位女警官太正义,以至于她太偏激。”
钱明说完了这些话,神情当中也有些疲惫。
我不晓得他是跟自己和解了,还是用这些话说服了自己。
他是大学的教授,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。
这些道理,他比我要更加清楚。
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就开始正常上班的普通成年人。
在我们那个年代,大学生比路边的野狗还要不值钱,物以稀为贵,因此贵就与我们不沾边了。
也许他说得是对的,因此他支持吴不知没问题。
也许他说得不对,只是安慰自己,自我欺骗,那也没问题。
身为他这短短的几十秒钟的听众,我耐心听完了他的话,不管认同与否,我向他点了头。
于是他对我露出了释然的神情。
轻声念叨了一句“谢谢”
。
随后站了起来,朝着房间外面走去。
他走后不久,正当我考虑是不是就在这里打地铺入睡时,周天乐慌慌张张地推门而入。
“他们都走了吗?”
“哎呀,我忘了跟你们说那边是休息的房间了。”
“现在跟我来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