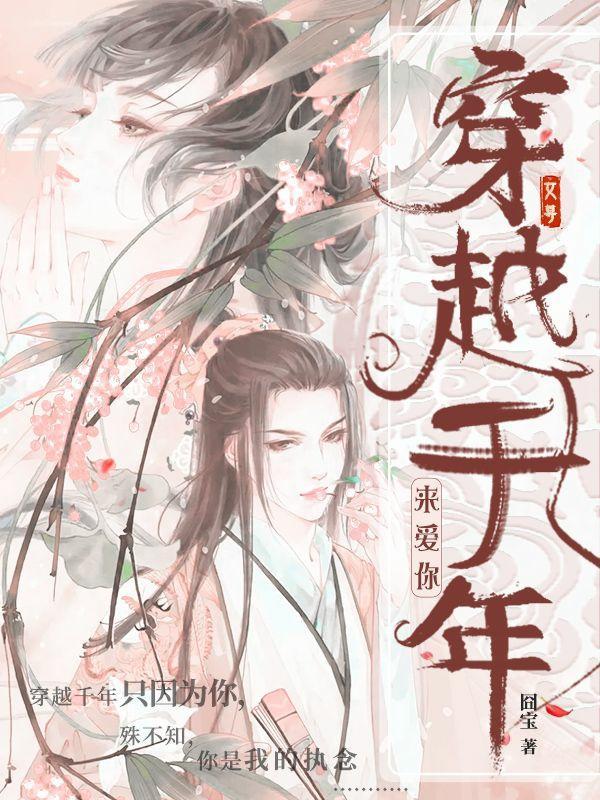多肉小说网>九锡 > 第881章 879妇人之见(第1页)
第881章 879妇人之见(第1页)
大齐鼎正二年,九月初七。
天空飘着蒙蒙细雨,冷风低沉似号。
年幼的天子李道明站在母亲身边,看着皇陵的石门缓缓落下,小脸上浮现一抹悲伤。
今天是山陵葬礼,是他的父亲落葬之日。
依照朝中重臣的商拟,经由两位太皇太后和他母后的同意,他的父亲被谥为哲宗睿皇帝。
李道明不懂这五个字的含义,他转头看着自己的母后,便见到母后双眼红肿,哀戚之情浓重如墨。
“母后……”
李道明怯生生地低声喊着。
宁太后深吸一口气,握紧李道明的手,转身望着祭坛上的文武重臣,视线在陆沉身上稍作停留,随即黯然道:“诸位卿家,回京吧。”
“臣遵旨。”
众人齐声应下。
宁太后最后看了一眼巍峨肃穆的皇陵,将所有的悲痛、茫然、害怕和疑惑压在心中最深处,牵着李道明登上御辇。
朝中文武相随于后,宫女、内监、禁卫熙熙攘攘,外围则有沈玉来亲自率领的五千禁军护卫,沿途有锐士营三千骑兵游弋巡视——这是宁太后特意下旨,命陆沉将锐士营带着,以震慑那些可能存在的漏网之鱼。
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回到京城,禁军和锐士营各自返回驻地,文武百官去往自己的官衙当值,新君因为这一趟仪程坚持下来很困乏,宁太后特许他去小睡片刻。
陆沉则进了皇宫,因为还没到京城的时候,宁太后身边的内监便传来口谕,要他入宫商谈国事。
文德殿偏殿,宁太后看着一丝不苟行礼的淮安郡王,温言道:“免礼平身。来人,给郡王赐座。”
“谢陛下赐座。”
陆沉没有矫情谦辞,通过这段时间在很多国事上的商议,他已经了解宁太后的性情,虽然他们也曾因为某些问题生过分歧,但宁太后从来不会含糊其辞云山雾罩,至少到现在为止,她都习惯用坦诚的态度和陆沉沟通。
“郡王,眼下大齐只能被动等待么?”
宁太后开门见山,直接询问她最关心的问题。
陆沉稍作思忖,缓缓道:“陛下,景国兵力多过大齐,而且他们通过灭赵和吞燕攫取了无数财富,这足以支撑他们动连续的战争。我朝无论兵力还是国力都要略逊一筹,即便有前几年的胜利,并未彻底改变齐景的力量对比。再者,景帝在攻伐代国之前主动收缩防线,便是为了防备我朝边军,因此我们小打小闹很难取得效果,反而会暴露我军的虚实,这就是当初臣不赞同出兵救援代国的根源。”
宁太后微微颔,不由得轻叹一声道:“不怕郡王笑话,哀家只是觉得这种滋味很煎熬,明知强敌磨刀霍霍,但是哀家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被动地等待对方大军南下。”
陆沉平静地说道:“陛下,其实朝廷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。”
“嗯?”
宁太后眼神微亮,问道:“郡王有何良策?”
李道明毕竟才五岁多,甚至还没到开蒙的年纪,让他这么早学习圣人大义和治国之道显然不可能,实际上他如今仍旧以健康长大为要,而学习这些道理的重任便压在宁太后肩上。
不光是在面对陆沉的时候,宁太后召见两位宰相和其他重臣时,都会抓住一切机会诚恳地向他们请教。
“陛下,打仗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比拼国力,又可以细化为三个方面。”
“郡王不妨细说。”
“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人、财、器。具体而言,人既指人才又含民心,陷阵之卒、领衔之将、决断之帅、运筹之臣乃至各个方面每一位人才,都能影响到一场战争的胜负。民心亦很好理解,取得绝大多数百姓的支持,朝廷才能整合出更强的力量,这就是臣等在江北制定严格军纪的原因,只有让江北百姓安心,他们才会想方设法支持边军。”
陆沉微微一顿,看着认真倾听的宁太后,说道:“举个例子,臣去年佯攻河洛实则领兵转向靖州的时候,便是定州百姓在各级官府的组织下,提前排查境内可能存在的景军奸细,让兀颜术无法及时收到消息,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”
宁太后信服地说道:“郡王言之有理。”
“财自然是指黄白之物,或许在很多大儒看来谈论金银俗不可耐,但是陛下您不能那样想。”
陆沉放缓语气,解释道:“将士们的饷银、赏银乃至抚恤银子,单看每一笔不算多,加起来却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,除此之外军械、甲胄、药品、粮草以及民夫和杂役各项支出,还要考虑到那些贪腐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,若是事先没有一个预估和准备,一场战争或许会拖垮一个国家,这就是先贤所言穷兵黩武。”
宁太后听得有些头疼。
陆沉观察着她的神情,继续说道:“至于器,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,比如将士们手上用的兵刃、身上穿的甲胄、守城和攻城时用到的各种器械,对于军队实力的提升不容小觑,但相对于前两项,这些东西只要交给可靠专业的人去做,便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”
宁太后沉吟片刻,逐渐品出陆沉的言外之意,试探性地问道:“看来郡王已经有了定计?”
陆沉答道:“陛下若相信臣,可以让臣尽快返回江北统筹练兵,臣保证景军南下之时,等待他们的至少是二十万敢战之兵。”